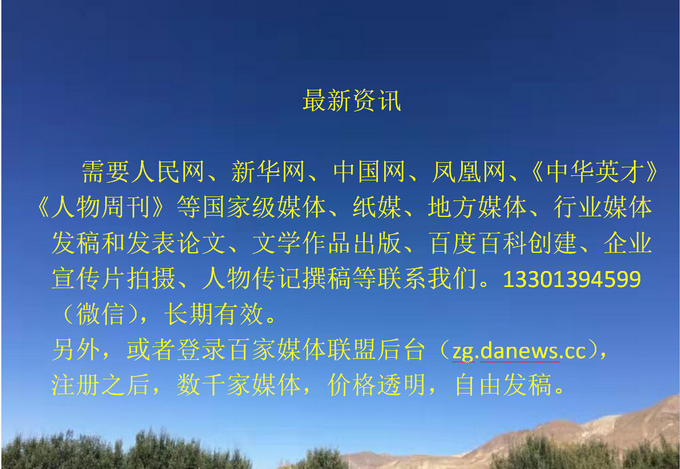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旅游诗歌旅游诗歌
野牛第4本诗集丨《公元1999》精选7首
发布时间:2021-11-12作者:来源:点击:
01
[ 老翁和少女 ]
春花遍野的时候,
东风阵阵袭人。
一个白发老翁,
路遇一个青春少女;
二人相视片刻,
彼此会心。
就在野地上
脱光衣裳;
艳阳晒着了他们身体的
所有地方。山野开敞,
天空蔚蓝,青青的草
和鲜妍的花,比人的身体不如。
老翁就干少女。
成熟繁复和青春单薄,
都是天然的尤物,
构成一种特殊的满足。
这是一种特殊的满足,
彼此便有了稀有的感受。
干完,各自示意,
在野径上分头走远。
1998年
—— 王子轩
—— 何炳阳
02
[ 播种 ]
春天来了,鲜花开了,
美丽的鸟儿四处飞鸣。
农夫挽起衣衫,把牛吆喝到田地里;
翻开冻土,播下春种,
轻描淡写的绿就生长出来。
青春来了,性欲满了,
繁殖的男女发情了。
男人脱光了衣裳到女人身上,
两个身子紧缠在一起;
温暖的春夜,有利于射精。
十月怀胎,
子宫的果实才最后生长出来。
1998年
—— 何炳阳
03
[ 今天我就要死了 ]
今天我就要死了,
虽然我还很年轻。
走在大街上,
我向一个妓女微笑,
如果在晚上,我会给她很多的钱。
可惜现在不是晚上,
我坐出租车 ,
在城里乱转。
亮着红灯的时候,
我要他接着开;
他笑笑说,红灯正亮着。
红灯和我有什么鸟关系?
今天我就要死了。
要是碰到一个警察,
我就给他一个耳光。
算了,警察也够辛苦的,
到地狱或天堂,
我还是带着一个干净的手。
走下出租车,
我丢给他几张100元,
我再也用不着钱了,
这种感觉真轻松。
来一个大将元帅,
我也可以不搭理地走我的路。
因为我要死了,死,
给了我最高的权力。
1998年
【领读】《今天我就要死了》,如果我没猜错,野牛应当是在酒后写的这首诗,尽管诗人已经有些“不省人事”,但诗中的“我”依然是真是可爱的。他走在大街上还不忘“像一个妓女微笑”,还会想到“如果是晚上,我会给她很多的钱”,打出租车时要出租车司机闯红灯,司机不同意,他还要强词夺理“红灯和我有什么鸟关系?”,甚至想到“要是碰到一个警察,我就给他一个耳光”“来一个大将元帅,我也可以不搭理地走我的路”这些真实的醉话,却真实地呈现着“本我”,而他之所以敢于这么狂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要死了,死,给了我最高的权力。”这首诗让人在诙谐幽默中,领悟生活的不易和心酸。
—— 王子轩
—— 何炳阳
04
[ 割草的人 ]
空地上爱长野草,
那人要种豆不让长草。
一有草尖冒出,
他就用链刀把它割掉。
可是刮了风,下了雨,
杂草又青青地冒出头脑。
那人又忙着割草,
把自己弄得腰弯背驼。
可是草偏要长,
即使不刮风,不下雨,
草也还在长。
那人只得守着割草,
割去一生七十年光景。
草还是长,稀奇古怪地长。
那人死后,草就长在他身上,
盖住了他的头骨。
还不如早就让它长,
青青地茂密地长。
虽然野草不是豆子,
在草原上放牧不也甚好?
为什么偏要种豆,
把自己累倒。
躺在草原上,看马儿吃草;
天空蔚蓝,风儿吹得很远。
1998年
—— 何炳阳
05
[ 读书人 ]
唉!倒楣的读书人,
发愤的读书人,
有点书卷气的读书人,
挺着脊梁骨的读书人!
读书人,
大多当不了官,
大多发不了财,
给妻子儿女
送了一份
无用的清白。
读书人,
好关心国家大事,
好以天下为己任。
可是读书人的家,
其实都很贫穷。
读书人,
也不见得就比别人聪明,
却老爱像教书先生那样认真。
一只翻动书页的手
跟官总是别扭。
那张不被山珍海味磨钝的口,
总是犀利地不饶人。
读书人,
就这样天生被人整。
商鞅闹着变法,
被人家五马分尸;
杜甫出去写诗,
把妻儿冻饿在家中;
清朝有个谭嗣同因为革命,
在北京菜市口被剁断了
脖颈。唉!天真无邪的读书人,
意气风发的读书人,忧国忧民的读书人!
读书人其实什么都不是,
读书人只是一介穷书生。
不过多一点思考,
动一点口舌,
好为别人道个公正,
好与社会论个清明。
外国人到中国来,
好在历史中找那些读书人。
有点书卷气的读书人,
天真无邪的读书人,
挺直脊梁的读书人,
倒楣的读书人!
1997年
—— 何炳阳
06
[ 河流 ]
河流不知从哪里来,
怎么就有了我。
河水泛着青光,
有时静而且凉;舒缓波及
岸旁。岸旁耸着树木和山岳,
飞鸟掠过我的头上,
我不能进入或者停留。我
在河水中日夜流淌。河水是我的故乡。
我们一意行走,到底要去向何方?
我们缘何要一起彼此沉浮?
是水推动着我,
还是我推动着水?
这里面是不是有更大的命运思想。
有人说顺流而下,
不推动它,不阻碍它,
完全和水一样。
浮在水中的事物,
真的能和水一样?
也许我这样想,就是一种叛逆和反抗。
在河水中,反抗,
确是一种最差的主张。
不管我怎样想,
河水总是日夜汤汤。
一些我身旁的物,
就消失了。
我也必然会消失,正如我突然就有了。
有前我为何物?
有后我为何物?
有中只能这样?
我想的时候,
夜晚早已降临,
满天的星光,
让河水更幽远地流畅。
深一般的黑,把我簇进梦乡。
梦中一些漩涡和着浅滩、岩礁和湍流,
仍在我的身边
冲撞。艳阳再度东升,
我又沉浮了一段时光。
如此浩漫的岁月,
不知还有多长?
1998年
—— 何炳阳
07
[ 谁是黄昌先 ]
她喊住我,在我们约定的操场边。
“黄昌先。”她喊我黄昌先!
我是吗?她很肯定地微笑着,
似乎有些亲热。一个叫黄昌先的人,
挨着了她。我以前叫过刘昌先,
我不知道刘昌先和黄昌先,
倒底是什么关系。反正她身上的雌气
喷着了我,我们拉着手,边走边谈。
可是这个叫黄昌先的人真的是我吗?
我老是不能肯定。他至多只是一个标签。
黄昌先是一个标签。
哪她在标签和我之间
究竟和谁亲着呢?
这个标签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就说明我父母姓甚名谁,
祖宗、国家源于何地?等等。
这样看来,我想的太远了。
这的确是一个太遥远的问题,
比卢梭那个孤独的农夫更遥远。
公元一九九九年的这个黄昌先,
不仅仅只是一个孤独的问题,
而是一个完全被混淆了本质的大问题,
一个被颠覆了存在性的大问题。
他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
靠在操场边的钢丝网上,我看着她
被雄性的身体激荡的样子,
忍不住想和她谈论这个问题。
可是当她的香吻压在我的嘴唇上时,
我又忘记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又想起,
还是应该提醒她。
怎样提醒她呢?
如果她知道了她热吻着的
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她该怎么想呢?
伤心,失望,迷惘,困惑?
我甚为难办。
幸好这时她说:
要熄灯了,走吧!
那就走吧。
1998年
【《诗鉴】
—— 何炳阳
编后记: